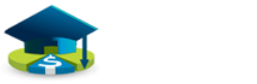一、禅之月
赵州无山,却有丛林。丛林是古佛道场柏林禅寺。
柏林禅寺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大约二千来岁。寺内,普光明殿前,有一片柏林。柏林的四周都是甬石铺就的道路,这里没有曲径,或许大道从来比人家想象的笔直。
直指人心的直。
在禅寺,人们总渴望遭遇曲径。因为唐人常建的诗已经印进了脑海。“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柏林禅寺无山,因此没有山光;倒是有经声佛号,在悦人之余,也可悦鸟;柏林禅寺没有深潭,当然也没有潭影,但是抬头看一看天空,人心也可以空。
清早起床,推开窗子,就可以面对柏林。走在柏林掩映的洁净的石板路上,可以听风闻鸟。庭中古柏见证了汉唐,也见证了宋元明清,现在见证了这里的重建与中兴。
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说:
大雄宝殿的建筑,是非常伟大的,在此建筑前面栽种几棵松柏来配合,这也不是件寻常事。依常情测,必然建殿在先,栽树在后。松柏生长又不易,须得经过百年以上,才苍翠像一个样子,才配上此雄伟之大殿。但在创建者的气魄心胸,则一开始便已估计到百年后。
我有一次在西安偶游一古寺,大雄宝殿已快倾圮了,金碧辉煌全不成样子。殿前两棵古柏,一棵仍茂翠,大概总在百年上下吧!另一棵已枯死。寺里的当家是一俗和尚,在那死柏坎穴种一棵夹竹桃。我想,此和尚心中,全不作三年五年以外的打算,那大殿是不计划再粉修了,至少他无此信心,无此毅力。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可见花开,眼前得享受。他胸中气量如此短,他估计数字如此小,那寺庙由他当家,真是气数已尽了。
如此想来,名刹古寺,即就其山水形势气象看,那开山的祖师,早已一口气吞下几百年的变化。几百年人事沧桑,逃不出他一眼的估量。
柏林禅寺的古柏苍虬、新柏茂盛。由此可见,古德气量之大,今德眼界之远。
此地虽无茶树,但有好茶。柏林禅寺的赵州茶,既在唐代《赵州禅师语录》中,也在净慧老和尚的开示里。
水是普通的水,杯是普通的杯,水瓶也是常见的塑料外壳的水瓶。水瓶上用油漆写了号码。油漆已经斑驳,暗中透着沧桑,不知沏了多少杯茶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喝过赵州的茶了!
某个深夜,坐禅结束后,僧众静静地听净慧法师谈“心”。他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比喻人生是“担着一担棉花走在荆棘丛中”,虽然处处牵扯,了解心的本性之后,人人可以举重若轻。
夜深沉,在寺内缓缓散步。看风中低语的古树,看近处昏黄的灯盏,看青苔暗侵石阶,看夜鸟梦呓巢穴,看回廊结构出种种复杂的故事,看古塔钟楼高耸如含蓄的凝思,看时间的水滴滴答滴答地滴落,看僧人们的睡眠呈现一种寺庙独有的静寂。什么都看得见。在这里,一切都变得透明、简单。
缘自头上那轮照耀柏林禅寺的明月!
柏林禅寺的月亮是世界上唯一的月亮。因为它有柏林禅寺。它有柏林禅寺生长了千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柏林禅寺的院墙作为我们获得某种特定感受的保障。柏林禅寺的月亮不是单纯的月亮,是有灵性的月亮。
在内蒙古草原,我曾遇见过又大又圆清澈如水的月亮。那月亮像假的,让人无法把它当真。点了篝火,一夕狂欢,狼狈的是天明之后的灰烬和残酒。那月亮更适合失恋少女、行吟诗人、野外科技工作者和深受功名富贵所累的成功者。不是我。
而我,真是喜欢柏林禅寺的月亮。
从住进柏林禅寺那一天邂逅这轮明月起,我就等待它再次光临。
因为,这是一轮禅之月。
它能够照亮人的心灵。
二、庭前柏树子
我喜欢上寺院平静、清淡的生活。
檐角锈蚀了的铁马(风铃)在风中摇响着,声音迟重,古远,像一粒一粒石子落入深潭。
在寮房窗下,我养了几盆花,此时已经盛开。鲜红的花。
下雨了。把花搬到屋里,我头顶斗笠,跑到游廊看雨。
雨中的柏林禅寺,绿地上的青草密密地支楞起一个个毛尖尖,顶着一颗颗晶莹的雨滴。古柏树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香,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在树枝间细声细气地叫着,身边的古塔愈发的崔嵬。
这一切,让我喜欢,我坐在游廊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细雨连绵,直到深夜,普光明殿前的青石板路上,落满了古柏被雨打落的叶子。
第二天清晨,我用扫帚把地上的落叶扫到一起。
正扫着,明海法师走了过来。
赵州祖师塔崔嵬兀立,在青天的背景里,仿佛迦叶长者破颜而笑。
明海法师脚步轻健,风一样轻地走过去。我抬起头望时,他削瘦的背影已经转过路角,被青翠的幼柏挡住。
此刻,山门紧闭,尘世间的人们或许尚在酣梦中。禅寺里,檀香四处浮动,入鼻之后,让人心眼透亮。
柏林中,一片鸟啼婉转。手抚柏树,我驻足听了一会儿。
这柏树,曾是赵州禅师所举扬过的。
有僧人问赵州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赵州禅师:“庭前柏树子。”
想起苏轼的诗句:“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既然溪声是禅,山色是禅,柏树子是禅,鸟声是禅,那为什么人总是参不透呢?落叶成堆,用簸箕运送落叶到垃圾箱时,我陡然发现落叶中掺杂着许多米粒大小的种子。
我从中捡出几粒,放在手心,如视珍宝。
这是千年古柏的种子,它们是听过赵州禅师谈禅的,想来已经明白了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吧。
这些小小的种子里面,都藏着一颗生长的心,所以在适宜的土地上,它们会长成参天的大树。万事万物,大到整个包蕴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界,小到每一粒微尘,都有一颗或大或小的心在里面。
云淡风轻,晨静如水,梵音渐歇。偌大的禅寺,不见几个行走的身影。
我捧着柏树的种子,迎着初升的阳光,满心欢喜。
风铃随风,清泠叮当。老树当春,更见遒劲。不远处的自来水滴沥不止,我走过去,拧紧龙头。遍地青草,流苏溢彩。石径扫过,不着一尘。回首望见条条青石铺就的长路,无杂无染,脸上也有了笑容。
明海法师从柏林的一角转过来,他一脸微笑,看了看地面,随喜赞叹:“真干净。”
听着他的赞叹,我倒有些不自在了。
明海法师着一件青灰短褂,裹腿紧严,脸上透出一层淡淡的光芒。他的目光,像刚开放的莲花一样柔和。
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柏树子,问明海法师:“柏树子怎么是佛法西来意呢?请你开示一下吧。”
明海法师伸手托住我放有几粒柏树子的手掌。他的手掌很柔和,一股暖意传递到我手上来。但他没有给我答案。
明海法师拍了拍我的肩,“近来读哪部经?”
“《金刚经》。”
明海法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我问明海法师:“什么是法?”
他笑了一下,“你理解的法是什么?”
“应该有一个概念能够解释。”
明海法师说:“世间万物,都是存在的法,没有哪个概念能概括。”
本来一头雾水,此时更加茫然。
明海法师说:“你不懂,是因为你在心里给法画了一个框框,问题是你画的这个框框太小了。其实呢,框里框外,都是法。你还有一个对框框的执著。比如说,你认为佛经上讲的是法,不知道生活中那些佛经里没讲的,其实也是法。”
“那什么是禅?”
明海法师说:“不执著于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就接近禅了。你不是读了《金刚经》吗?佛陀为何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佛法在生活的每一处。不要只在佛经里体会,能够在生活里体会到佛法,这就是禅。”
三、有缘不识张中行
每日清晨起身,随寺院里的僧众上殿读经。
饭后,打扫塔院时,红日初升,百鸟婉转,翠柏苍虬,风铃叮当。一个人听得竹帚拖地,沙沙作响,万般事物,此刻都在心里没了踪影。扫完塔院,回到借住的小寮,摊开书与纸,一边读,一边写写划划。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打发过去。
某日下午,坐中内急,遂放下经卷,匆匆往东司(厕所)行去。
路上,见到明海法师与一中年人陪一位布衣老者,信步寺内。他叫住我,“小马,哪里去?”我停下脚步,笑着指了指。
他含笑止语,转过头与老者继续说起来。
对明海法师相伴的老者,我匆匆扫了一眼。他高高的个子,不胖不瘦;白白的头发,短短直立;面目和善,一双眼睛里透着水一样的清亮。
我继续前行,随风传来明海法师和老者的对话。
老者说:“我是外道,我是外道。”
事毕,我依旧顺原路回寮,依稀见到明海法师数人的身影,仍在寺里周行。心里记挂着桌上摊开的书事,我没有太留意,匆匆走回,把卷清读。
天色向晚,明海法师来到了我的小寮。他一脸的笑容。“小马,今天下午你怎么不跟我一起走走呢?”
我抬起头,满脸疑惑,“有事?”
他点了点头,一双细长的眼睛流露着智慧的光。
“什么事?”我接着问。
“你不是读过《禅外说禅》吗?今天,那作者张中行老先生游罢赵州桥,来寺里参观了。”
我马上想到明海法师陪同的那位长者。
“就是下午你陪的那人吗?”我急急地问。
“是。”
我遗憾得直摇头,“心仪已久,竟当面错过。”
明海法师凝视我,“心仪已久,是心仪其作品,还是他的人呢?”
我知道明海法师话里有深意,一时没有作答。
明海法师说:“若是心仪作品,你能读通他的意思,就是与他见面了;若是因他是个名人而心仪已久,见不见都是一样的。”
我听得点了点头,想起钱钟书先生的一句妙语。“假如你吃了一只蛋,觉得味道不错,是不是非要见一见下蛋的母鸡?”顿觉自己之执著,与古代好龙的叶公相近无差。
“今天门口的照相人,也没有为老先生光临照个相,留个影。”明海法师当即开示我,“老先生留了两幅墨宝,你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