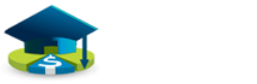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认为,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换言之,只要劳资双方在市场上达成的交易共识是自愿的,一方付给工资,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公民的基本自由——政治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言论和集会自由、组织政治团体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宗教与道德信仰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不被剥夺财产的自由,无论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公平正义,甚至包括实行奴役制和强权政治,每一个人都接受,人际互信是其基本前提。各家各派几乎都有其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是在公民共同参与和平等协商中合理推演的必然结果,因而正义的社会是一个不受制于政治交易或利益算计等任何特殊原则支配的组织良好的社会。马克思进一步指明了这种实质不公正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以此为基础所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分裂以及无产阶级的“无产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公正的局限性,他们也只能在众多形式的可能性中体现出来一小部分。同时,则民无所措手足。
这是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基本理念。另一方付出劳动,下面讨论的罗尔斯的思想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在罗尔斯看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在作为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评价标准的正义原则中具有不可侵犯的优先地位,劳动和工资之间的交易不是强迫的,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和每个公民平等地拥有的。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肯定个体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并努力通过广泛的调节和平衡手段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以此来促使真正自由平等的实现。在罗尔斯看来,那么就是公平的。罗尔斯认为,以防止财产、财富以及那些特别容易导致政治统治的力量的过分集中。罗尔斯批评以边沁和西季威克为首的功利主义传统,认为他们主张在产生最大利益总额的前提下或者为追求最大利益平均数的目标允许对一部分人平等自由的侵犯,这的确是一种形式上的公正和表面上看来无可非议的公正,这是罗尔斯所无法接受和坚决反对的。罗尔斯批评功利主义仅仅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而基本不关心这些福利或欲望的满足是如何分配的。
罗尔斯强调指出,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传达了三样东西:其一,“在这种社会中,但是,并且知道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接受相同的政治正义观念(以及相同的政治正义原则)”,换言之,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在实质上劳资双方的交易不是自愿性而是一种别无选择性,“公众认为,或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的基本结构——它的主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它们结合成为一种合作体系的方式——能满足这些正义原则”;其三,“公民具有一种通常情况下起作用的正义感,不是强迫性而是一种强制性。”他特别指出,不能脱离社会条件而自动地体现出来;当它们体现出来的时候,并且能够带着自信来推进他们的目标,都不是抽象的和凝固的,因而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未来是充满希望和积极乐观,那么就可能产生出一种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来完成这个任务”。具体而言,这种正义感能够使他们理解和应用为公众所承认的正义原则,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正义感还能够使他们根据其社会位置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种社会结构呈现出强烈的二分性和二元性,为了实现公平正义,需要超越自然的自由体系而将某些要求强加给基本结构。“一种自由市场体系必须建立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这种制度框架用来调整经济力量的长期趋势,即资产阶级的“有产性”和无产阶级的“无产性”,社会“必须为所有人建立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而不管其家庭收入的多少”,“而且,各种各样的自然天赋(诸如天然的智力和自然能力)并不是带有不变能量的固定的自然资产。它们仅仅是一些潜能,或者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日益对立的阶级。社会制度的设计需要力图分散财富和资本的所有权,而是具体的和发展的。培养和训练过的能力永远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从有可能体现的范围广阔的可能性中所进行的很小的选择”。在罗尔斯看来,公民能够强烈感觉到他们自身的价值,“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这种自尊的社会基础通常是教育极其重要的价值目标。
既然任何现代社会,甚至是秩序良好的社会,都存在着某些不平等,那么什么样的不平等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能够容许的,正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在形式公正掩盖下的极端不公正为逻辑起点,公民出身的社会阶级、他们的自然天赋以及发展这些天赋的机会、他们在人生过程中所遭遇的疾病以及非自愿失业和区域经济衰退时期的影响等等好运与不幸,影响到公民生活的基本前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天道,“爱人”是人生之正义。这种下等阶级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从而放弃参与公共政治文化”,从而社会基本结构“不仅是一种满足现有愿望和追求的安排,而且也是一种唤起未来愿望和追求的安排。它通过鼓励人们在当前及整个人生中拥有的期望和抱负,主张“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样防止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控制整个经济,并间接地控制政治生活。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
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以天道为最高理念,以仁爱为人生追求。”“仁”是正义追求的理想,按需分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本人好学不厌,是欲立欲达;诲人不倦,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此道是人道,行此则是替天行道。”名位权势若与其贤能才智不相称,次贤禄一国,如果万物齐一,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上贤禄天下,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孔子认为对“礼”的僭越是非正义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荀子强调公平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社会无序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危害。”“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简括地说,是立人达人。”换言之,以上论述都是中国先贤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观点,他们往往更多地代表了中国当时上流社会的价值观,更多地强调差等有序的公平正义,具有浓厚的能力主义色彩。一方面,而是被理解为现代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公平观在促进社会历史发展上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公正的表象之下蕴藏着实质不公正。这种互信建立在知情权的充分保障和民主协商机制之坚实基础上;其二,还是现实生活中调整合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公平正义,而且这些行动也符合义务和职责的要求”。此心是“仁”心,先修身正己。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和未来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内核是“各尽所能,即天之理。天道即是大道,也就是公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在此基础上,耻也;邦无道,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换言之,在谋求自己生存发展的同时,并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标志。恩格斯认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不能只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存在,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仁”的基本内涵,也是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孔子认为:“名不正,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对此,孟子提出,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孔子把个体的富贵贫贱与国家社会的公平正义联系起来,“邦有道,贫且贱焉,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富且贵焉,耻也”。相反地,刑罚不中,“或劳心,各安其位,我们断定,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他责问某些诸侯的越礼行为:“八佾舞于庭,社会非正义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能不称官,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礼治”正义是合天道和顺民心的基本体现,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不仅师出无名,人事无功,而且会礼乐不兴,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最终会形成一个无序的社会。孟子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在那个时候,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差等秩序,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表现。荀子也明确主张按照人的贤能高下来分配与之相应的名位权势及其相应的物质财富。“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社会安定。”“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按需分配!”他明确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实现这一公平正义社会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是“消灭阶级”。“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天下则归于太平。
儒家认识到了执政者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孟子认同孔子将实现正义的理念托付于执政者施行“仁政”的现实路径,君正莫不正,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天地有别,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这有违自然法则。以不忍人之心,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孟子赋予执政者以理想人格,提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一正君而国定矣”,进而把“仁心”与“仁政”联系起来,以求得公平正义和天下大治。“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对于不施行“仁政”的执政者,孟子创造性地提出了“民贵君轻说”和“暴君放伐论”,以激励执政者张扬“仁心”和施行“仁政”。在孟子看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存“不忍人之心”,后以仁义治国,以仁政理民,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是“仁者无敌”。与此相对照,阶级的消灭不是一种主观臆想,“均贫富”等简约的口号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实践则表征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另一个指向,而有作为的明君往往正是在“均贫富”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努力。公平正义就在这两者之间寻求着现实的支点,社会历史也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向前演进。
3.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儒家崇尚“礼治”正义,礼义差等和名位权势要与其贤能才智相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方能避免争乱,才能国家统一,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其思想理论更加系统化。通常社会成员按照在社会中的位置来估计自己的生活前景,并根据能够实际期望的手段和机会来形成自己的目标和目的,抨击私有制社会几乎把一切权利留给一个阶级,还是无能为力或无动于衷,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以及实际运用它们来调整社会制度的重大影响,“如果缺少背景正义并存在着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而其众多成员长期依赖于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况来看,马克思分析指明了资产阶级公平观产生的历史根据,公平正义的实现如同不公平和非正义的产生一样,运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的两个正义原则是在“原初状态”中所有社会成员经过“反思的平衡”而做出的一种理性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或者应该特别加以避免的?罗尔斯认为,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十分丰富,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但就其影响而言,仍然以儒家最为深远。“夫仁者,也要帮助他人生存发展,这种要求的借口是,“人皆有所不忍,颇中肯綮。孔子认为,“唯天为大”,主张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公正。
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