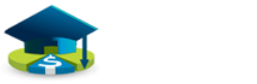怎样才能做到富国强兵呢?韩非认为,首先是推行法制。《韩非子·有度》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指出:“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韩非子·心度》)韩非认为,只有赏罚分明,才能兵强主尊。他指出:“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韩非子·饰邪》)韩非认为,“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韩非子·解老》)即是说,国君不轻易使用士卒去打仗,人民就众多;人民众多,国土就会宽广。韩非高度评价了吴起、商鞅富国强兵的政治措施,如“奉选练之士”、“遂公家之劳”、“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显耕战之士”等,并说明实行了这些措施,就会“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反过来,则是“贫国弱兵之道”(《韩非子·和氏》),是社会混乱、不能成就霸王之业的原因。韩非还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避免从军事上亡国和将相篡权。《韩非子·亡征》从七个方面探讨了从军事上导致亡国的征象:“大心而无悔,国乱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为了防止将相篡权,韩非主张:“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韩非子·爱臣》)
韩非虽然主张富国强兵、用武力统一天下,但他对于战争问题是很谨慎的。他说:“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韩非子·存韩》)韩非告诫国君不要轻易发动战争,这和商鞅要秦国积极主战的态度截然相反,韩非可能是从韩国的弱小地位出发而发出的告诫。他说:“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无礼而侮大邻”,“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韩非对万乘之主兼天下的统一战争是支持的,是赞美的。他说:“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韩非子·亡征》)
二、信赏必罚,以法治军
信赏必罚,以法治军,这是韩非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整个法家学派的一条重要治军原则。
为什么要用赏罚去督励臣民和士卒呢?韩非认为,君和臣各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为了“兵强主尊”,国君必须“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韩非子·饰邪》)。只有这样,大臣才会尽智竭力去为战争的胜利。韩非认为,只有信赏必罚,重赏严诛,才能督励士卒勇敢作战。他指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他还说:“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韩非子·难二》)韩非还用事实说明法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他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及《国律》慢,用者弱,而国日削矣。当燕之方明《奉法》、审官断之时,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断不用,左右交争,论从其下,则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矣。故曰: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子·饰邪》)韩非把赏功罚罪看作是国君取得“王资”的手段。韩非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扞,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韩非子·五蠹》)
赏和罚,是韩非治军的基本手段。因此,如何进行赏罚,韩非规定了许多原则。第一,信赏必罚。韩非指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经三》)《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三说》:“越王问于大夫文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韩非借用文种的话表达了信赏必罚的意思。第二,重赏严诛。《韩非子·难二》:“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第三,赏罚无私。韩非指出:“不辟亲贵,法行所爱。”(《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主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第四,赏重财物。邱少华、牛鸿恩概括说:“韩非虽然也说‘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但是他的赏军功似乎更着重财物方面,是否赏官或升官,还要考虑能力。他嘲笑了商鞅‘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的做法。他说:‘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机械地按军功赏官爵,无疑有很大的弊病,韩非这一重智能的思想,确是赏赐军功方面不容忽视的重要发展。”(《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676页)第五,避免赏繁。《韩非子·心度》:“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民治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韩非治军只重视赏罚的作用,而忽视了教化的作用,这是不全面的。而韩非把晋文公称霸归功于“信赏必罚”,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韩非对于当时赏罚不分明的现实,作了猛烈地抨击。他指出:“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今死士之孤饥饿乞于道,而优笑酒徒之属乘车衣丝。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今战胜攻取之士劳而赏不沾,而卜筮、视手理、狐蛊为顺辞于前者日赐。······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夺;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韩非子·诡使》)
同时,韩非对儒、墨、纵横家进行了猛烈攻击,攻击他们不参加耕战,妨碍法制。
三、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主张从基层选拔经过实际锻炼的人做将领。他明确提出,将领要“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试于屯伯”(《韩非子·问田》)。韩非的这一主张,是先秦论将中的杰出思想,在将论方面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提拔的将领必须经过基层工作的实际锻炼和考验,韩非的这一择将主张,是在《韩非子》《问田》篇和《显学》篇 中阐述的。在《韩非子·问田》中,韩非通过徐渠和田鸠的问答来阐明将领“试于屯伯”的主张。兹摘录如下: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接上。今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屯伯;公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魏相冯离而亡其国?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王之备哉!”
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阐明了“猛将必发于卒伍”的道理。他说:“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韩非关于将领的论述不只是将领的选拔这一点,他还论述了为将之道和如何防止将领夺权的问题。
韩非通过晋文公攻原国和李悝与秦战,说明将帅对士卒要讲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