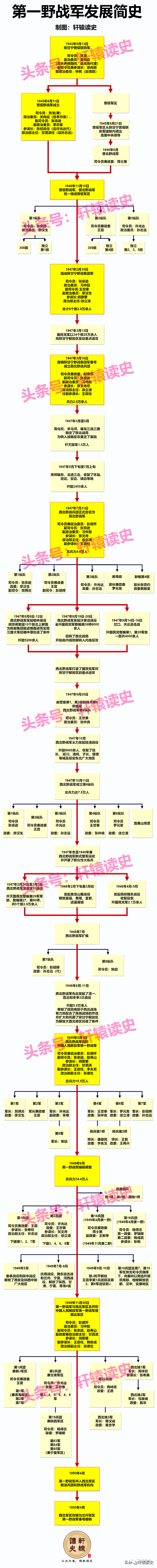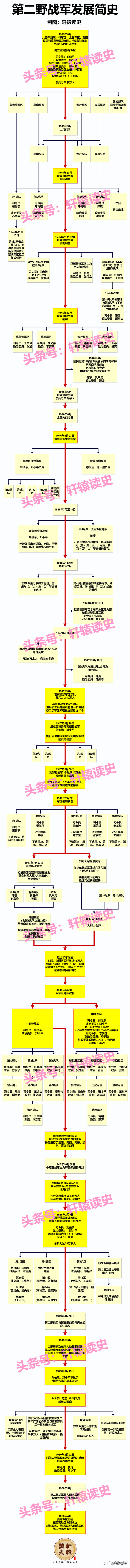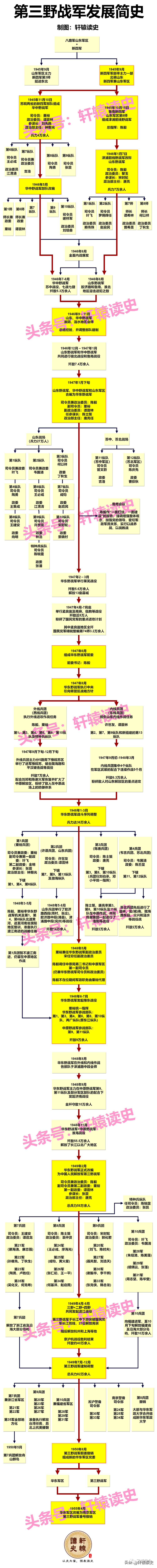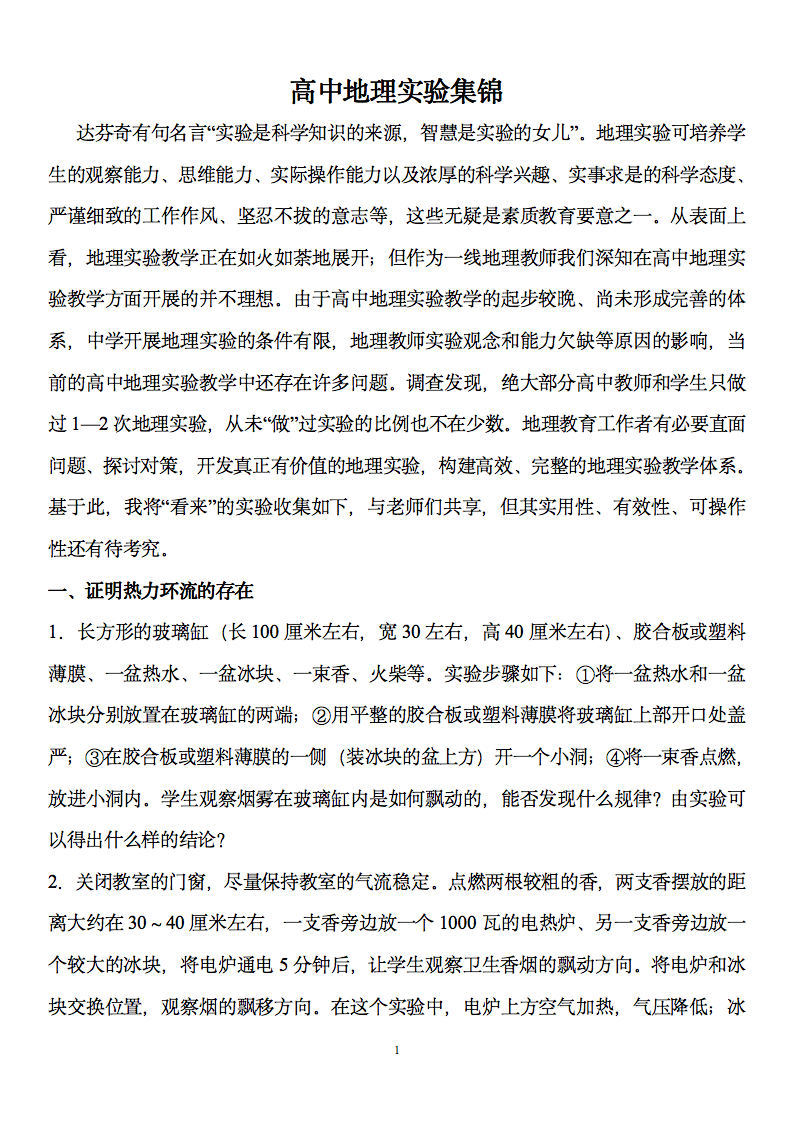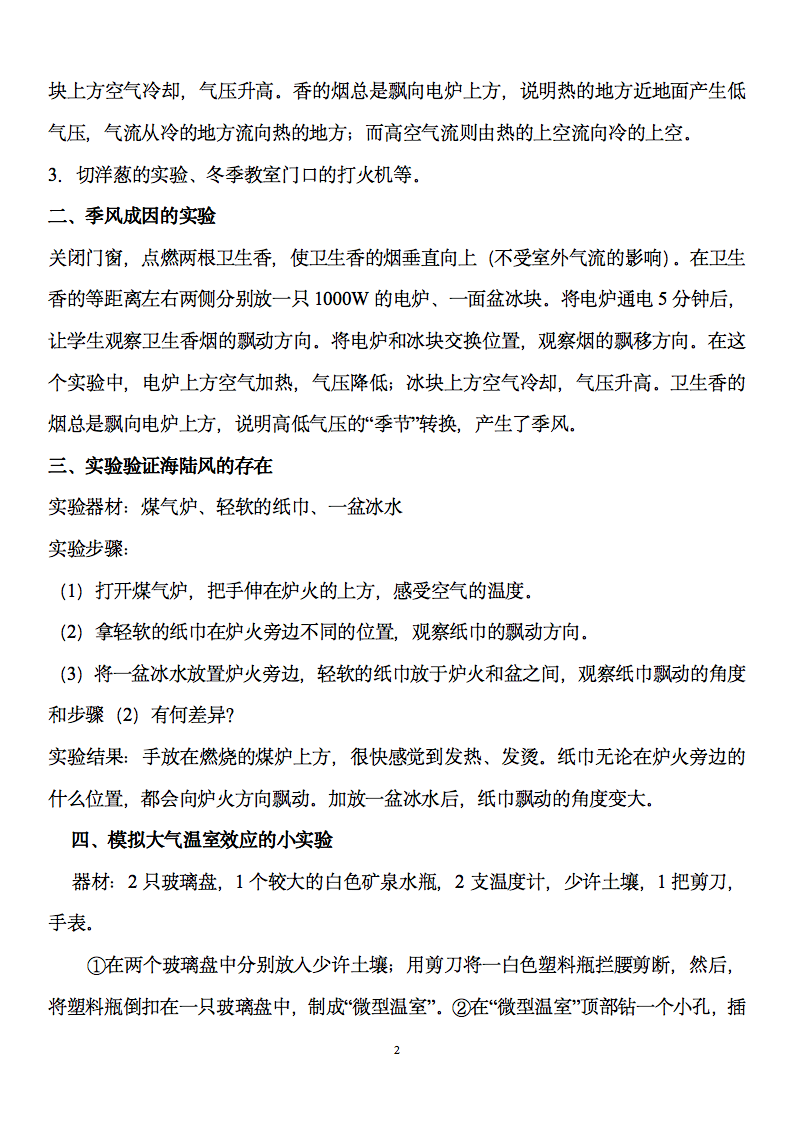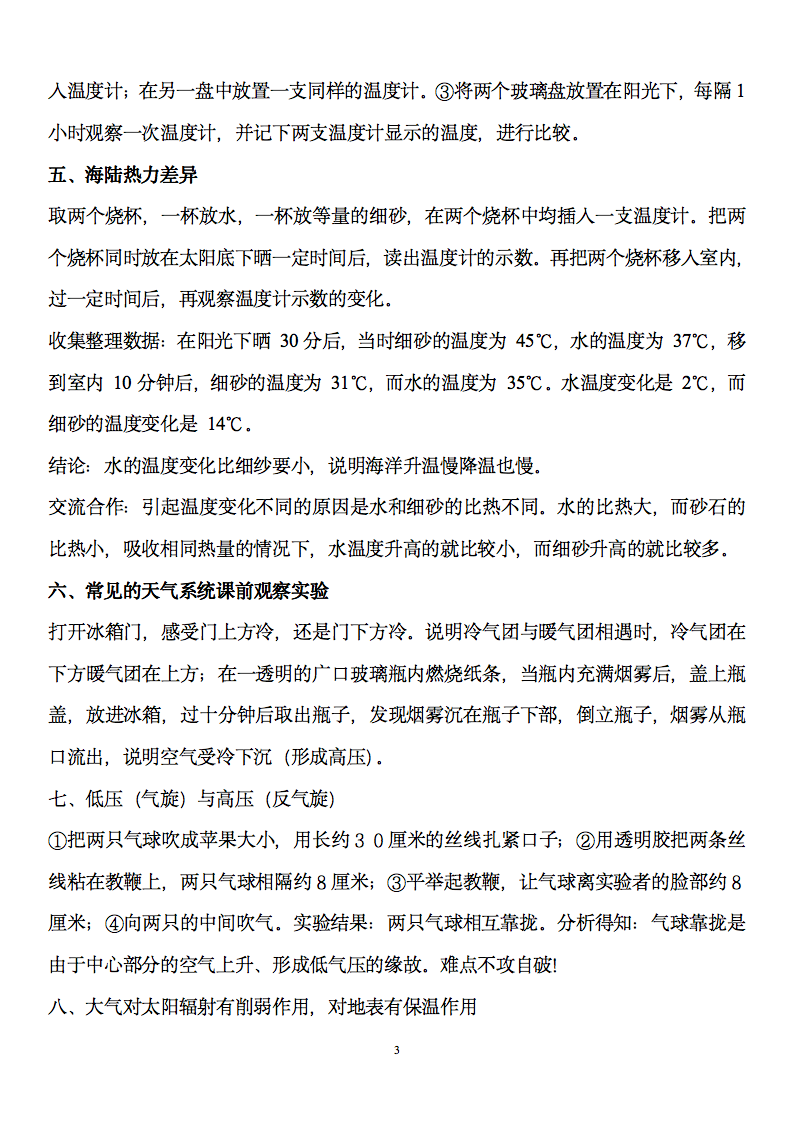田纪云:因祸得福,丢了一支枪没受处分,还升了级,捡了个老婆
推荐语:
田老的这篇文章真实生动,亲切可读,虽然平铺直叙,读来却能见人物见故事----
我的青少年时期
作者:田纪云

田纪云,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本文摘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的前言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闲来无事,不由自主地想想这,想想那,也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这里我想主要回顾一下走进中南海之前的日子,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总的还算一路平安。
我的家庭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六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一九五零年这个乡改为汶阳镇,隨第一区划归肥城县管辖)。田家东史村座落在山东省泰山西南约四十公里的大汶河北岸。这里是太肥山区中仅有的一片盆地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人所称“汶阳之田”即指此地。

位于汶阳镇田家东史村的田纪云旧居
我的家庭在当地算是个名门望族。我的祖母生下我父亲兄弟姊妹十一人,七男四女,一男一女小时夭折,活下来九个,六男三女。抗战前,全家人口已达三十二口之多,且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有我的曾祖母(曾祖父英年去世)、祖父母,我的父辈兄弟姊妹及我们这一代。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当过乡里正(即乡长),知书达理,崇尚文化,为人正直,不信神教,不崇洋人,乐善好施,广交朋友,思想比较进步,重视儿孙们的文化学习。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在兄弟中排行老大,一九二七年就读于济南省立高级师范,以后又在泰安县城里教书。我二叔田晋臣(原名田锡廷),继我祖父在当地当乡长。三叔田锡贞在家经营一小中药店。四叔早年夭折。五叔田锡珉、六叔田锡琰、七叔田笑海(原名田锡珊)三人在家务农,他们有的上过中学,有的上过小学或私塾,都有一定文化知识。我的父亲,在父辈中是学历最高的。他性格耿直,为人憨厚,但不善交际,一生在曲折坎坷中度过。他在泰安县城教书期间,我的祖父、叔父们背后多称他是书呆子,认死理。
“田家军”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东的济南和泰安。在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泰西地区抗日峰火四起,一九三八年,我父亲和我二叔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父亲任政委,二叔任队长,三叔、七叔和我大哥也先后参加了这支队伍,在泰山南部大汶河一带打击日伪军,被当时泰西人民称为“田家军”。一九三九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二叔在率部行军途中,与泰安县城出来扫荡的日军遭遇,不幸被俘,当即被押送泰安日本宪兵队监狱。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受尽了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但他视死如归,从未屈服,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于一九四零春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立即西渡黄河,直奔冀鲁豫边区一专暑参加抗日工作。
随着形势的变化,我父亲先后任泰西县抗日政府民教局长、冀鲁豫边区聊城专暑文教局长、聊城中学校长、菏泽中学校长、冀鲁豫行署文教处教育科长等职。一九五三年,他在担任菏泽中学校长期间,据说在给学生上课时讲了江青的什么坏话(后来才知道,是说江青原来不叫江青,叫蓝苹,与毛主席结婚是康生介绍的,并说中央对她有约法三章,不许她过问政治等),菏泽地委书记与他个别谈话时谈崩了,一气之下他辞职回家。一九五四年,菏泽地委派人又把他请回去,给了他撤职处分,分配到单县中学任教。文化大革命他被调到河南省洛阳市六机部所属柴油机厂的职工中学任教,又因上课时讲了什么“错话”被打成“反革命”。
父亲革命一生却被打成反革命,蒙受不白之冤,我帮助父亲写了申诉书,后经平反,办理了离职手续。
我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性,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很有教养。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也是我读私塾时的老师。抗日战争前母亲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以身作则,勤勤恳恳,很受妯娌们的尊重。父亲参加抗日工作后,不论父亲处境如何,母亲都与之相随,照顾父亲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因父亲与我们弟兄三个都先后参加抗日工作,母亲整天牵挂我们,思虑过多,患上了失眠症。一九七一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机关,就将父母接至成都一起生活。那时,我们缺乏医疗知识,听人说服安眠药有副作用,千方百计不让母亲吃安眠药,老拿维生素片骗她。她彻夜失眠,万分痛苦,终因心力衰竭于一九七三年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其实,她一个家庭妇女,又不管国家大事,糊涂点又咋的!为什么不让她多活几年!我真是后悔莫及。
一九八一年,我调到国务院工作后,把父亲迁来北京。他老人家一九九一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少小投奔八路军
一九四零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月,周边一些大的村镇也被日本人设为据点,我的家庭多次被查抄。这时我的家人已不能在家正常生活,有的投亲靠友,有的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我随母亲有时躲在外祖父母家,有时躲在大姨家。一次在汉奸带着日本人查抄我家时,我和二叔家长子田纪霞、三叔家长子田纪雯三人都跑到一家近邻躲藏,三叔家比我长一岁的田纪雯被汉奸认出,当场枪杀。这时我们在家再也呆不下去了,亲戚家也都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们。于是,一九四一年冬,刚满十二岁的我便和二叔家刚满十三岁的田纪霞一起,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可爱的家乡,西渡黄河,奔赴冀鲁豫军区第一分区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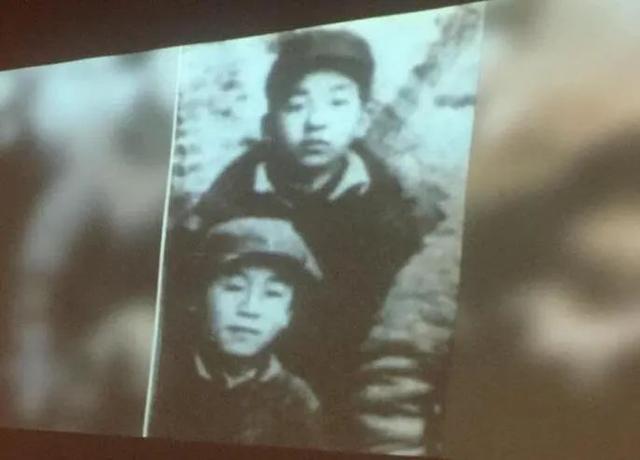
1945年与堂兄田纪霞在一起
为了使负担分散一点,我先是投奔七叔任参谋长的独立团当了一名小八路,田纪霞直接去了二叔任厂长的八路军一分区所属抗属工厂。独立团团部的同志对我都很好,我七叔有时让我当通讯员,有时让我到厨房帮炊事员洗菜,老号长有时拉我去教我吹号。但就是夜行军不行,一上路就打瞌睡,七叔常常把马让我骑,但我打瞌睡会在马背上掉下来;七叔有时把我栓在马尾巴上拉起走,也会打瞌睡摔到沟里去。无奈,半年后,七叔把我送去抗属工厂当了童工。这个工厂主要是为部队生产地雷、手榴弹,也织袜子、毛巾、熬肥皂。在工厂我学会了翻沙浇铸手榴弹弹壳、织袜子等。工厂员工多系工农出身,有文化的不多,我这小学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了,教大家识字、唱歌。干了近一年,组织上认为我们年龄小,又有一定文化基础,可以培养,送我和田纪霞到山东茌平抗日县政府领导的抗属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完全是抗日家属子弟,实行供给制。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根据形势经常流动。
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多次被化整为零充当农民的孩子。中国农民真好,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我们。日本人一扫荡,就马上要我们穿上他们孩子的衣服去地里干活,拾柴、捡粪,或躲到他们的亲戚家。这期间,我在聊城一带共认了五个干娘。所谓“干娘”,就是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对长辈男性叫“老大爷”,对女性长辈则叫“老大娘”,久而久之,感情深了,就直接叫“娘”、叫“爹”了,并没有举行过什么认干娘的仪式。这时的我,深深体会到,人民群众之于共产党,犹如树之根,鱼之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八十年代,我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赴聊城地区考察工作时,曾有意去当年呆过的地方看望这些老人,但都早已辞世,只能见见他们的后代。

199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到山东临沂九间棚村视察
一九四五年初,我被保送到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直到一九四六年末。“第三抗日中学”处在鲁西南游击地区,学校有时在黄河南,有时在黄河北,经常流动。学校也很少上课,有时听听形势报告,发点教材自己看。大部分时间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护理伤病员和征收公粮等,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就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我还不满十六岁。我一入党,就当上了区队长,发给我一支日本造三八大盖,站岗、放哨、征粮都扛着它,一直扛到离开三中。
在三中,在一次战勤工作中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夫人的李英华(我们都被派去照顾“二野”第一次陇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她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大姐、大哥都于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参加抗日。她与我同年参加抗日工作,先于我到三中学习。她是三中的高材生,考试经常名列榜首,我呢,要么第二,要么第三。那时在根据地有文化的女孩子不多,有不少大干部想接近她,但她都不予理睬,而偏偏爱上了我这个无依无靠、背井离乡的穷学生。李英华的母亲是抗日家属,吃救济粮,经常节省几毛钱给李英华,她就悄悄地给我,实在馋了,就赶集去吃个烧饼,喝碗胡辣汤。

田纪云同李英华婚后第一张照片,1949年2月摄于菏泽
一九四六年冬,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带领工作组参加朝城县(今莘县)一区的土改与扩军工作,我任工作组长兼区长。在土改与征兵工作中我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动员96人参军)。其间也曾被借调到朝城县委宣传部办油印小报,自编自刻自印。这时我也经常给《冀鲁豫日报》投稿。《冀鲁豫日报》有个编辑叫王效文,是我父亲的同学,对我的投稿,不论用与不用,他都仔细修改后退我,并指出问题所在,要注意什么,对我帮助很大。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被派去冀鲁豫会计学校学习会计业务,随后我的未婚妻李英华也到会计学校学习。年末毕业后我被分配隶属冀鲁豫军区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这是我第二次参军。李英华被分配到冀鲁豫九专署财政局工作。
淮海战役带担架队支前
一九四八年秋淮海战役打响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带领担架队支援前线。我担任担架营营长,担架营共八十副担架,每副担架三个人,轮流抬。担架队员多是老根据地的民兵或农村积极分子,有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有高昂的支前杀敌热情。战斗打的很残酷,部队伤亡很大。担架队的任务是把包括敌方的伤病员从前线抢救下来,送到野战军医院。担架队队员都具有很高的觉悟,在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我个人也和队员一样,上前线背伤员。
在担架队完成任务回程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我带领的担架队来去执行了五次任务。完成任务返回根据地时,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有一天,夜幕降临,担架队露宿在离今菏泽市约三四里路的王楼村,一说不走了,大家都席地而睡。我呢,警卫员给我找了一张破席子铺在路边上,又找一块砖头做枕头,我把手枪皮带压在砖头下边,就呼呼睡去。当天亮醒来时手枪不见了。我非常恐慌,几乎问遍担架队的所有人,都说没有见。第二天,我带着十分慌恐、沉重的心情回到战勤总指挥部。当晚就向党小组作了检讨。我们会计科的科长崔子平要我写书面检查,以便报告指挥部领导处理。第二天,我正在写检查时何光宇司令员(老红军,开国少将,建国后曾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把我找去谈话,把我臭骂一顿,说,你这混小子,怎么没把你自己丢了。我哭着请求司令员处分我,什么处分都行,但千万别开除我。我说,我一家人都在外干革命,我回家会饿死。司令员说,你去写检查吧!我写检讨的过程中,崔子平科长走来劝慰我。他突然问我,小田,昨天司令员骂你了没有?我说骂了,骂的很厉害。科长立即说,小田,你别哭,司令员骂你,就可能不会处分你。崔子平科长告诉我,当他骂你的时候,可能是信任你了,要用你;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给你倒茶,那你可能要倒霉了。他还举了多个例证。我将信将疑。大概是第三天,命令下来了,提拔我为正营职会计,总务科为我配备马一匹,司令员还让他的警卫员送我一支德国造手枪。
当时部队有个规定,当了营长以上干部以后可以结婚,但对方必须是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不能随军。因为快要渡江南下了,所以我与我的爱人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就结婚了。这件事很快传开了,战勤指挥部的人都说,小田“因祸得福”,丢了一支枪,还升级,捡了个老婆。事后我知道,战勤指挥部党委研究,念我年纪小,思想纯洁,又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做出来提级、配马的决定。

20世纪50年代初的田纪云,1950年摄于贵阳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八年,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八年中,我当过兵、做过童工、搞过土改征兵、带过担架队等,这些经历既锻炼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也造就了我坚强的毅力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八年砥砺,使我由一名小八路成长为一名南下干部。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2